扬州八怪之独特艺术风格揭秘

#走进博物馆#
扬州八怪究竟“怪”在哪里,说法不一。
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怪。
八怪本身经历坎坷,他们有着不平之气和对贫民阶层深深的同情;他们对丑恶的人和事加以抨击,或著于诗文、或表诸书画。
但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多少见,但也不少见,因此不足为奇。
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怪。
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,他们正常的和官员名士交流,参加诗文酒会,也没像晋代文人那样放纵、装痴作怪、哭笑无常。
所以,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“怪”也是没有道理的。
那么就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了。

郑燮《金农诗横幅》
知我者梅也的李方膺
李方膺的画笔法苍劲老厚,剪裁简洁,不拘形似,活泼生动,作品纵横豪放、墨气淋漓,粗头乱服,不拘绳墨,以瘦硬见称。
李方膺在八怪中的成就不亚于郑板桥和金冬心。一生最爱梅花,画梅花直至生命尽头,在他的传世作品中,将近一半是梅花题材,所画的梅花用笔苍劲老辣,构图简练疏朗,挥毫纵横,水墨淋漓。

如《故园秋色》,用笔老辣,墨色多变,运笔有力,落笔准确,从浓到淡展示出墨分五色的隽永雅致。
菊花用淡墨描绘,墨色淡而不暗勾勒出花形,花瓣没有填染颜色,让朵朵菊花尽显光彩,仿佛在阳光下顽强生长。

又如《墨梅图》,枝干挺秀,倾斜多姿之韵。构图简练,以水墨染枝干,淡墨勾勒出花瓣,浓墨点蕊,虽寥寥数枝,而疏影暗香已极尽其致,浓淡相宜的墨色与造型苍劲相映成辉,古趣盎然。
用狂草笔法作画的黄慎
黄慎的笔姿荒率,设色大胆,以狂草笔法入画,变为粗笔写意,行笔“挥洒迅疾如风”气象雄伟。点画如风卷落叶,并打破书画的界限,将画竹画兰之法融入书法之中。
黄慎将草书融入笔下的人物,虽然受到形象的限制,但是无论对象坐立行止还是俯仰转侧,喜怒哀乐还是庄严诙谐,无不形体准确,神情生动,巧合人物的身份和内在感情。有时即使寥寥几笔,也极为准确生动。

如《美人图》,人物比例准确,墨色浓淡相宜,衣纹用笔迅疾狂放、线条顿挫,用笔大胆泼辣,有扑朔迷离中见神韵之感,充分展示了黄慎高超的笔墨技巧和以草书入画的绘画特色。
人物虽无娇艳之色,但却另有一种素静、典雅的清韵,这种不重形而重意态气质的描绘,正是黄慎人物画的一个特点。

又如《探珠图》,以狂草线条作写意人物,造型生动。笔线纯熟酣畅,无论是降龙取珠的老者,或是体态婀娜的女仙,性格的刚柔,形体力度的对比,均表现得传神得体。
大片水墨的渲染,显出云绕浪涌,更造就了奇险的气氛和勇猛的境界。
有人赞叹黄慎的作品笔墨流露出文人的书卷气,自由张扬,彰显个性。也有人贬低黄慎身上没有“士气”,不能入名雅之流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黄慎是中国人物画乃至国画界能够如此集中、如此大量地用世俗题材表现下层劳动者的第一人。
善作山水园林小景的高翔
终身布衣的高翔,山水取法弘仁和石涛,所画园林小景多从写生中来,秀雅苍润,自成格局。
高翔擅山水花卉,在他笔下山水花卉成了寄禅情托禅思之所在。他的画风可以分为两类,一是单纯山水花卉;二是在描写中有禅景出现的图形。
单纯山水花卉通常为写生,有弘仁、石涛笔意。萧疏简洁,空旷幽深,山石多用线条表现水墨稍加渲染,简淡清秀,规整中见狂放。

如《山水图卷》,将写实与抒情相结合,运用疏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“桃花源”。画法上继承了黄公望、倪瓒的传统,但又融会贯通,自成一格。
山石均以“披麻皴”画出,略作苔点,几乎不用渲染,笔法简括疏秀,墨色淡雅,写出了山水的空灵之感。
树木大多双钩枝干,树叶或圈或点,墨色清润,表现出江南草木润泽的特征。
而狂放之笔意,不仅是石涛的启迪,更是其超脱尘世进入禅境后心灵自由的生动表现,是高翔用直白的方式对内心向往禅境的图式建构。

如《弹指阁图》,画中的场景“弹指阁”是高翔的一处书斋。院中老树树叶线勾墨点浓淡互衬,右边“弹指阁”在芭蕉、竹林的掩映下,更见幽雅之韵。
人物虽寥寥数笔,却栩栩如生,给人一种超然脱俗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。行笔错落有致,淡墨勾润,浓墨点视,清疏中流露出一股秀逸的气息。
此外,“扬州八怪”虽是各怀才艺的文人画家,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,绘画对于他们并不只是自娱,他们也不拘于封建文人的儒雅气质,而是与商人合作,顺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喜好,所谓“俗中带雅方能处世,雅中带俗可以资生”,与传统文人相比,确实是怪了。
——未完待续——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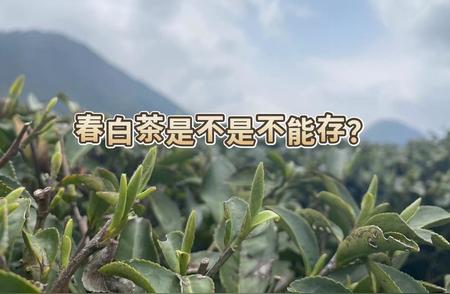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7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7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