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晖解读《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》全新视角

“猪八戒是黑猪还是白猪?”“孙悟空吃没吃过人肉?”“取经路上挑担次数最多的是谁?”“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,是不是得了失忆症的妖精?”这些入门级的问题,可以检验我们先前读过的《西游记》是不是一部假书。
“向唐僧传授《心经》的,是观音还是乌巢禅师?”“‘观音老母’的称谓从何而来?”“发兵剿灭刘洪的是殷开山还是虞世南?”“《大闹天宫》和《安天会》是一部还是两部戏?”“鬼子母和嫔伽罗,罗刹女和红孩儿,这两对母子有什么联系?”这些貌似莫名其妙的问题背后,有一个更大的“西游故事”传统,需要我们仔细发掘。
有一个真相绝非不言自明:“西游故事”,并不等同于百回本《西游记》里的故事汇总。
《西游记》的历史若以万历二十年(1592)世德堂本为起点,就已有四百余年。若是将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里玄奘获《心经》的记载,或敦煌S.2464号卷子里观音授《心经》的传说作为原型,那么这个国民超级大IP的故事体系,则远在世本诞生前就已枝繁叶茂,此后仍然不断发展演化。
迄今为止,以百回本成书与内容为中心,并围绕它关涉的各类先期文本(antecedents)和后期衍生文本而展开的研究著述,可谓琳琅满目。然而,以百回本之外的“西游故事”为研究主线的专著,却较为罕见。《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》(赵毓龙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6,以下简称《跨文本研究》)就是依照后一种脉络进行系统梳理,并聚焦于杂剧、宝卷、神书、西游戏、鼓词等非小说文类,通过文本的平行比较,总结西游故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渊源传承、发展特征和表现差异。这可以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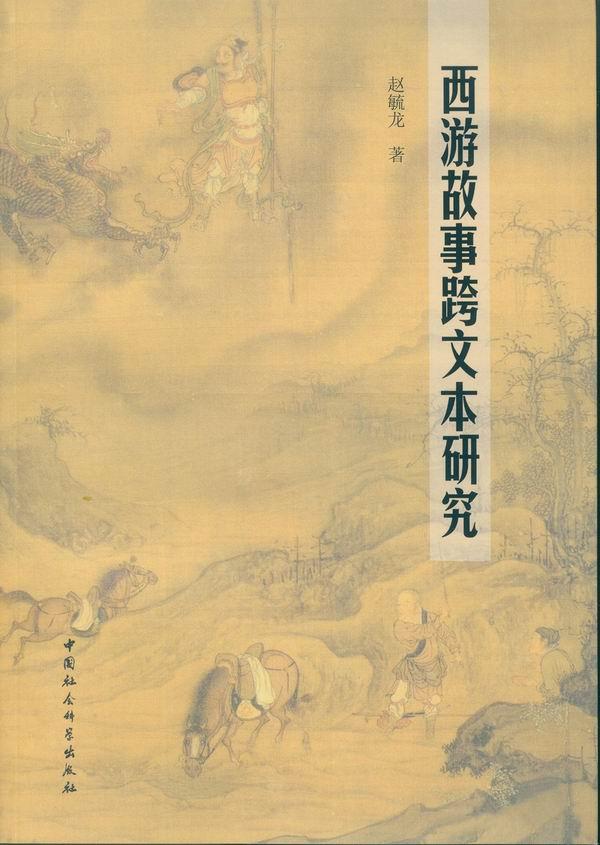
《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》
百回本被冯梦龙列入“四大奇书”,标志着它在通俗文学领域内经典地位的确立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游故事的封闭定型化。但百回本成书阶段内未予吸收的众多素材,以及这些次级故事的传播途径,仍还保持着旺盛活力,并继续承载着众多异质叙事元素和语域功能。
举例来说,江苏地区香火神会使用的神书,至今保留着有别于百回本的“袁樵摆渡” “魏征斩龙”“唐王游地府”“刘全进瓜”“九郎请神”“殷秀英骂贼”“唐僧取经”等“唐忏”内容(车锡伦,《信仰·教化·娱乐: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》,学生书局,2002,331-332页);以彩色纸为衣冠道具的彩绘泥塑唐僧师徒,1994年在安徽天长县的农村丧葬仪式上仍有使用(车锡伦,《中国宝卷研究》,广西师大,2009,80页);戴步章老先生1989年口述扬州评话《西游记》,还大讲特讲“吊桶奘缧缧藤,扁担长的杨辣子,坑又坑死人,砖头子又成精,瓦砾子又作怪”这些“神话小说当中都谈到”、但在百回本里遍寻不到的“一些事情”(易德波,《扬州评话探讨》,江苏人民,2016,425页)。江淮神书又有相似表述:“逢到砖头也作怪,遇到瓦砾也成精 ……扁担长的洋腊子,吊桶精的罗罗腾。”清代西游戏和子弟书对“才子佳人”情节的渲染和伦理道德的强化,鼓词对色情细节的沉迷耽溺,又体现出特殊的时代需要。(赵毓龙,181页,245-261页,285-297页,304-309页)
《跨文本研究》的时间范围截止至清末。它从文本演化的角度,对于诱发多元阐释冲动的早期传统和内在属性,对于西游故事在不同时期和受众层的传播形态,都多有概述。这给当代情境下的西游文化研究也会带来有益启发。
这部书的最大贡献,是将关注点转移到以往不甚重视的边缘性文本材料,并且试图建立它们的内在关联。借用作者的话,就是“克服百回本本位观以及小说系统本位观的消极影响”,“以戏曲文本系统和说唱文本系统为中心”。它对西游戏曲资料的整理研究,堪称详实丰富,尤其值得称道。
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虽是语言文字资料,但也意识到“愈来愈多的文本被扩充进来,不唯有小说、戏曲、说唱,还有史传、诗文,而在文字形态之外,更有图画、雕塑、器具等立体文本。”(赵毓龙,第8-10页)毕竟“文本是一种最普遍的人类经验对象。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基础,确实由它们而构成。”(Jorge J. E. Gracia, A Theory of Textuality : The Logic and Epistemology, SUNY, 1995, p. xiii)从传统文本的盘绕根柢里滋蔓丛生出的西游文化,或显或隐地存在于当代符号世界里。

《中国宝卷研究》
即使是在本·海默尔所谓现代“日常生活的日常性”包围下,这些文化因素也会以奇异的方式,在“无人察觉、毫不显眼、不甚分明”的“无特质之特质”里呈现出来。
两年前我去超市买菜,无意间瞥见生鲜冷柜里的一款山黑猪肉,发现它竟然有一个极具风味的品牌名称——“精气神”。这家公司官网的Logo里还有谜语般的题铭:“古今感悟精气神。”
我猜这三个字的典故出处,应该是明嘉靖三十四年(1555)《清源妙道显圣真君忠孝二郎开山宝卷》的韵文:“唐僧随着意马走,心猿就是孙悟空。猪八戒,精气神,沙僧血脉遍身通。”整个文本“反复说唱的是如何修炼内功和这部宝卷的‘灵应’”(车锡伦,2009,144页)。胡适在《西游记考证》(1931年)里比较过它和《销释真空宝卷》的生成年代。余国藩先生的英译《西游记》修订版序言里,引用道教内丹典籍《性命圭旨》的“三家相见图”。图中就有“身心意是谁分作三家,精气神由我合成一个”的文字。(Anthony Yu, The Journey to the West, Univ. of Chicago Press, 2012, Revised Edition, p.85-86)结合百回本里对八戒的描写:“黑脸短毛,长喙大耳。”一头寓意丰富的黑色野猪形象便跃然眼前。
能够不显山不露水地把文化内涵如此深刻的名称赋予一块山黑猪肉,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材。
后来我跟某位笃信中医养生的好友聊起这件事,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又让我瞬间石化:“猪肉性寒,入肾和膀胱经,滋阴润燥,填精益髓。”根据中野美代子在《〈西游记〉的秘密》里的说法,猪八戒同时对应着内丹术五行体系里的水和木。木与肝相关,水和肾相关。
有谁能够想到,传统与现代、文学与饮食、宗教与日常的关联纠结,会以如此“意味深长”的形式出现呢?
窥一斑而推全豹。通过这个旁门左道的事例,不难想象以百回本为中心的研究局限。世本里虽有诸多类似的寓意暗示,却找不到“猪八戒,精气神”等对应语句。可见百回本只是西游故事在某个演进阶段的成果。它既不是故事源头,也不是演化终点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小说形式从来都不是“西游故事”的唯一载体,文字阅读者也不是唯一受众类型。以百回本为中心的文本阐释,自然无法公允评估西游故事传播过程中的多种差异和流变现象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《跨文本研究》里蒐集的各色资料,以及较为细致的文本分析,足以拓宽视野和思路。

余国藩英译《西游记》
不过,这部作品里仍然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首先是它的总体架构模式。
作者既然想要摆脱百回本中心论的影响,最好能够形成相对新颖的切入点和篇章结构。从著作标题里,可以看出对“跨文本”分析的倚重。然而这个模式相对模糊宽泛,作者也承认它是“西游学界的传统研究视角”。继续停留在这个视角,并运用“互文阐释”进行罗列点评,难以让人真正感到耳目一新。
作者进一步梳理的演化分析脉络,即“由本事到故事,由低级形态至高级形态,由情节链条到故事群落的线性轨迹,以故事化、世俗化、传奇化、小说化、群落化、神魔化、通俗化等演变机制为着眼点,讨论不同属性之文本系统在故事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” (赵毓龙,14页),同样显示出传统论述与材料归类方法的刻板影响。这种影响在前四章安排上格外明显。
“唐五代:西游故事的发轫期”“宋金元:西游故事的聚合期”“明:西游故事的定型期”“清:西游故事的赓续期”。这种按照朝代顺序形成分析框架的做法,在处理材料时会带来不必要的限制。作者在序言里强调的“横向”比较,尤其是不同时期和文类的贯通融会,也不便展开。事实上,只有到第五、第六章的个案考察时,作者才能够完全摆脱以往研究套路的束缚。
另外从材料取舍方面来看,应当区分其轻重巨细。单以第一章为例,许多史实材料跟取经故事虚构化进程的关系不大。使用较多篇幅讨论,其实并不经济。我们必须看到,从史实到取经故事,再从取经故事到西游故事,是极少量史料的高度虚构化和演绎过程。例如,几乎所有的虚构故事均略去玄奘私自出关这一历史细节,转而强调他正式受命取经的身份。余国藩先生称:“这种将取经人与唐王朝联系在一起的虚构叙事,在[百回本里的]取经活动前就已经展开……虚构的取经人系世间最高权威者所派遣的事实,彻底改变了[历史]玄奘的身份和故事讲述模式。”(Yu, p. 56, 58)第一章里《法师传》《独异志》和敦煌卷子关于玄奘获《心经》的记述,以及后世文本袭用的“摩顶松”传说,是比较有价值的材料。其余多数内容则跟后几章的材料难以形成贯穿续接。
在我个人看来,与其罗列关系不大的背景材料,不如分析与西游虚构叙事关联更密切的佛教典籍。例如禅籍、净土宗文献,以及唐代至明代的仪轨和忏法文本,都是宝卷形成的来源之一(欧大年著,马睿译,《宝卷: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》,中央编译,2012,22-28页);再如,邵平最早指出百回本“悟空拜师”与《六祖坛经》具有直接文本关联,这些在西游文本的叙事分析方面或可派上用场。
作者在“跨文本”范畴下交替使用“故事化、世俗化、传奇化、神魔化、通俗化”等“着眼点”,由于名目众多,又存在诸多重合,显得错迭散乱。有些像“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”这类头衔,着实让人记不仔细,而且容易牵扯出不相干的材料,产生疏松堆砌感。
如前所述,全书第一章着重讨论了玄奘的“传奇化”。但这般伟岸的人物形象,为何在第二章的“神魔化”和非人类角色介入后产生质变,作者并没有给出满意解释。由于同一时期还存在“传奇”这种专门文类,使用“传奇化”这个不甚严谨的概念名称,来概括寥寥几句的史料或笔记内容,并不是很妥当。
再如,作者声称文人在西游故事传播中扮演了“距民间思想更近”的中介角色,又认为通俗化是“文化品位的下移”。其实在古代俗文学发展过程中,雅俗界限与交互作用,并非单向的下移这样简单。文人笔记被作者视为“雅”,而神书里一些性隐喻描写,比如孙悟空向唐僧诉苦说自己被压五行山下,只露出脑袋,所以经常遇到“乡里大娘挑野菜,一屁股坐在脑壳来”,则被视为“粗鄙恶浊”。然而明初陶宗仪的史学笔记《南村辍耕录》,明明就记载了“锁阳生鞑靼地”等不可描述的类似场面,还被《本草纲目》正经八百地引用过。西游故事的通俗化或雅化研究,目标应该不在于评估其品位高低,而是要考察它为了达到特定效果而采取的有效、具体的手段。
总的来说,作者的“跨文本”研究经常是在同一时段、同一角色、相同或相近文类范畴内展开的平行比较。因此还可以用更灵活、更深入的方式,充分展开跨越历史阶段和文类界限的探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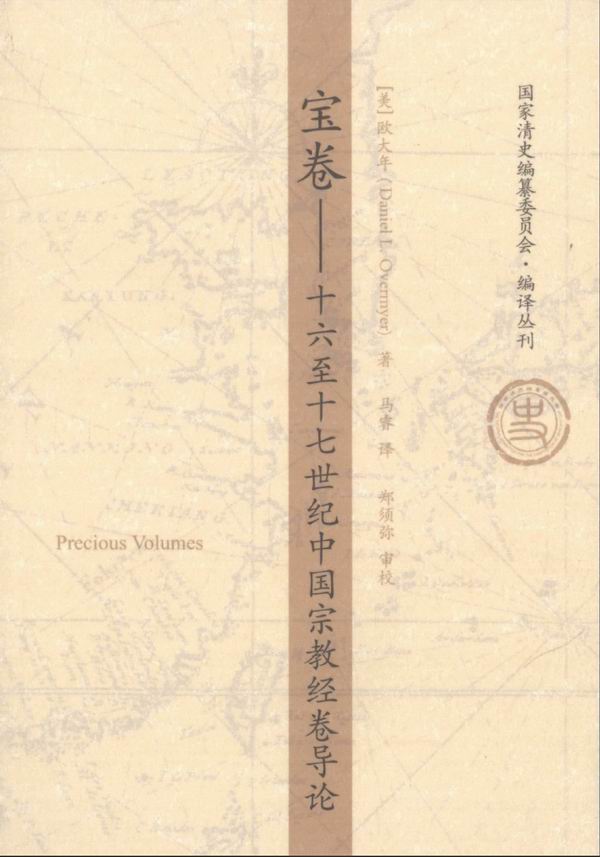
《宝卷: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》
那么,在这些关联文本之间,应该采取哪一种更合适的“跨”法?
作者自己提到多数西游文本里不可或缺的两个考察维度,尤其值得重视:一是神魔“斗法”模式,二是围绕“斗法”而进行的人物性格塑造。在我看来,如果能有机整合这两个维度,或许可以更清楚展现不同文本的叙事差异与关联,从而理析出跨时代、跨文类、相对普适的通约性(communicability)。可惜作者的分析着眼点过多,这两个原本应该重点讨论的维度,始终不够突出。另外,从普洛普的角色类型划分开始,再去分析情节、意蕴,这个研究顺序有些本末倒置。
神魔斗法的情节模式,源自佛教典籍有关降伏邪魔外道、显示佛法奇能的记载,后来衍生出“僧道斗法”等套路(赵毓龙,124-129页)。表现斗法场面,必然要引入形形色色的人物、法宝和法术。在西游故事的口头和书面传播过程中,简单的情节架构、神通表现和普通角色形象,通常难以满足读者或听众的欣赏需求。玄奘形象在《取经诗话》发生根本转变,虽然能解释为故事世俗化过程中重新赋予的“刻板形象”(赵毓龙,121-125页),但不足以体现这种转变对西游故事演化的贡献程度。
我们不妨认为,由于斗法情节的升级加码需求,猴行者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这些个性鲜明、具有非人类属性的行动者,开始从不同故事来源逐步介入,并形成角色层次和行动配合关系。按照师徒五人的能力差别,作为普通人类角色的唐僧被置于底层,但他反过来能用紧箍咒修理能力最强的悟空。这就形成一种复杂有趣的循环制约关系,它非常适合灵活设计(甚至临时调整)各种“共同御敌”时斗法、斗气、斗嘴的情景,并通过语言、文字或舞台表演而制造冲突、渲染气氛、抒发情绪,或启人深思。
再看其他几个例子。
百回本之前形成的《二郎开山宝卷》,叙事中心原本是二郎神。这属于《跨文本研究》里所说的“他源故事”。余国藩先生称,“诚如杜德桥指出的,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不曾犹豫为小说引介所有新的、不相干的神话与历史传统”,例如“二郎神、北方真武、哪吒,以及李天王的故事” 。相比悟空这样的“要角”,“天宫地府的诸佛仙圣数量虽然庞大,却不过是陪衬或支撑叙事的角色” (余国藩著,李奭学译,《〈红楼梦〉〈西游记〉与其他》,三联书店,231-234页)。但在《二郎宝卷》里,二郎救母与唐僧取经这两个“不相干”的情节,形成了“救母”与“取经”的叙事关联。这种“孝子”形象的塑造,以及它和“取经”行动的关联模式,在百回本和其他西游文本里继续沿用。一些关键寓意词汇和意象(“二郎守金炉,炼着牟尼珠”“照妖镜,照魔王,六贼归顺”),与后期西游文本里的“闹天宫”和“诛六贼”等情节也多有照应。但是,角色重心已经从二郎神偏移到唐僧和悟空身上。
元代吴昌龄杂剧《二郎收猪八戒》的基本情节,与百回本的“高老庄收八戒”颇为相似,但有明显差异。剧中集体出现了唐僧、孙悟空、沙和尚和火龙,猪八戒则是冒充朱公子摄走了裴员外女儿裴海棠。裴海棠在第二折称,八戒原是摩利支天御车将军,“诸佛不怕,只怕二郎细犬”。斗法的高潮部分,是二郎神放细犬咬住八戒,责令其保护唐僧西行取经。剧中悟空扮作裴小姐戏耍八戒的细节,在百回本等西游故事里得以保留和渲染。二郎神擒八戒的细节,则转移到“大闹天宫”部分。如果以“斗法”情节的安排需要、“要角”人物的再塑造以及整体叙事效果为考察主线,就可以对这些不同时期、不同文类的作品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比较。《跨文本研究》第三章第一节里对“准西游故事”《二郎神射锁魔镜》的情节分析,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。

《〈红楼梦〉〈西游记〉与其他》
本书的第三个问题,是对西方理论的一些偏颇理解。
“近年来,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阐释本土文本的研究方法逐渐为学界所摒弃,而从实际操作上讲,以某种叙事学贯穿始终的设想,是不可能实现的,也是无必要的。”(赵毓龙,11页)事实是,作者在进行具体文本分析时,除了明确声称的“部分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”外(具体指E.M.福斯特的情节观和普洛普的“角色”类型理论),仍不得不频繁借用经典叙事学的诸多理念框架。
从理论工具的运用和发展来看,完全没必要进行硬性的“东西”划分。叙事学确实源于西方,但它的分析对象,尤其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,针对的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文本材料。
再者,叙事学也并非单一封闭的理论体系,中国古代叙事文本的特性,反过来正好有助于推动叙事理论的完善发展。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学的专门研究,申丹考察直接、间接引语和转述语在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片断里的作用,商伟采用叙述者分析对《儒林外史》的阐释,都是东西兼顾、理论和实证有机结合的良好范例。
赵毓龙先生对“西方理论”概念和体系的理解偏差,还体现在其他方面。例如对“故事”“情节”“叙事”的区分不足;对“历史叙事”“历史话语”和“宏大叙事”这些词汇的不当应用;用小说分析方法来解释戏剧念白的视角关系;对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的错误判断等。
作者数次引用福斯特的“绦虫”(tapeworm)比喻来形容故事形态,却既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暗含了福斯特对“故事”(story)和“情节”(plot)的区别定义,也没有看到自己频繁使用的“情节”一词往往只是福斯特说的“故事”。对于福斯特的理论局限,尤其是他与叙事学主流的概念差异,应该也未加注意。“重视结构关系的叙述学家……将情节视为故事中的结构”,而福斯特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对事件的叙述,情节应侧重于因果关系。这一区分标准,“极易导致混乱”。因为“如果故事事件在作品中起了一种骨架的作用,即使不具因果关系,也可称之为情节”(申丹:《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》,北大出版社,2004,51-53页)。西游故事里的诸多事件,未必都构成明显的因果关系,福斯特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。
再如,作者借助形式主义理论家普罗普的叙事学研究方法,对人物进行了角色功能的概括分析。结构主义叙事学多采用归纳法,而普罗普根据叙事中的行动功能,从数量庞大的民间故事里提取出“角色”类型。但这种归类方法,容易将人物完全变成“从属于行动、由行动予以定义的‘行动者’”。普洛普的理论,也不是什么“新的方法或视角”。在他之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探讨故事结构时,“均把注意力放在事件或行动的(深层或浅层)结构上,而不是放在人物身上”,因为“行动是远比人物要容易归纳的叙事层面”(申丹,62页)。不同时期、不同文类的西游故事里,同一名称的人物很可能具有千差百异的属性。从《二郎宝卷》和《二郎收猪八戒》的例证可以看出,单个角色形象建构的背后,某种行动模式在不同文本和角色间的转移挪用,才是更具代表性、更深层的现象。《跨文本研究》隐约意识到普洛普的局限,却仍然拘泥于角色类型的机械区分和标识。
我们不妨再看看“互文性”、“互文阐释”和“跨文本”这几个出现频繁较高的术语词汇。
互文,或互文性,是当代文学理论里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。互文研究最早源于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,并通过克里斯蒂娃而完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,因此前后定义和关注范围存在明显差别。在使用“互文阐释”这种术语时,有必要界定清楚是哪一种意义上的使用,而国内许多研究者常常把“互文”当作万能词汇,在使用时几乎完全不加辨析。
最早提出“跨文本”这个术语的,则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。热奈特在《覆写文本》(Palimsests)里声称,“诗学的研究主旨并非单独状态下的文本……而是原文本(architext),或不如说,是文本的原文本性……是从一整套普遍或超越性的范畴里(各种话语类型、阐述模式、文学体裁),产生出每个单独的文本”,他将这种原文本性归入“跨文本性”(transtextuality)的大范畴之下,后者是“对于文本的文本式超越”。跨文本性可大致定义为“确定某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或显或隐之关联的全部内容”。艾伦认为,这是“热奈特版本”的后结构主义“互文性”(intertextuality)。但热奈特在“跨文本性”的范畴下,又重新界定了另一种有别于后结构主义的“互文性”。它是“两个文本或多个文本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”,是“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内的实质存在”。例如引用、剽窃或用典。这就不再是后结构主义强调的“互文性”(“文化与文本意义上的符号学进程”)(Graham Allen,Intertextuality, Routledge, 2000, p. 101)。《跨文本研究》在使用“互文”和“跨文本”这两个关键词汇进行具体文本分析时,前者接近于热奈特的互文概念,后者时而趋向于“原文本性”的探寻,时而又偏向文化研究的角度,更像是后结构主义的“互文性”概念。由于未进行有效界定,相关论述很容易让人迷惑。
前面说过,热奈特的“互文”前提是“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内的实质存在”,从而引发读者或评论者展开合理阐释行动。《跨文本研究》有时候泛泛使用“互文阐释”一词,有时又忽略可能存在互文之处。例如张本、朱本和高本《唐僧取经》神书的“高老庄”段落里,有“上坟”和“三月初三游春”的不同表述,被认为是全无关联。但如果考察寒食、清明、上巳节的来历,就会发现两种行为的联系可能。
专业研究者需要切实把握诸多资料文献,更要有严谨的理论支持。“道不须臾离,可离非道也。神兵尽落空,枉费参修者。”百回本里这段关于兵器的寓意描述,可以用来形容理论分析工具的重要性。在了解不足的情况下,以中西之别为理由而排斥有效工具,是不太明智的做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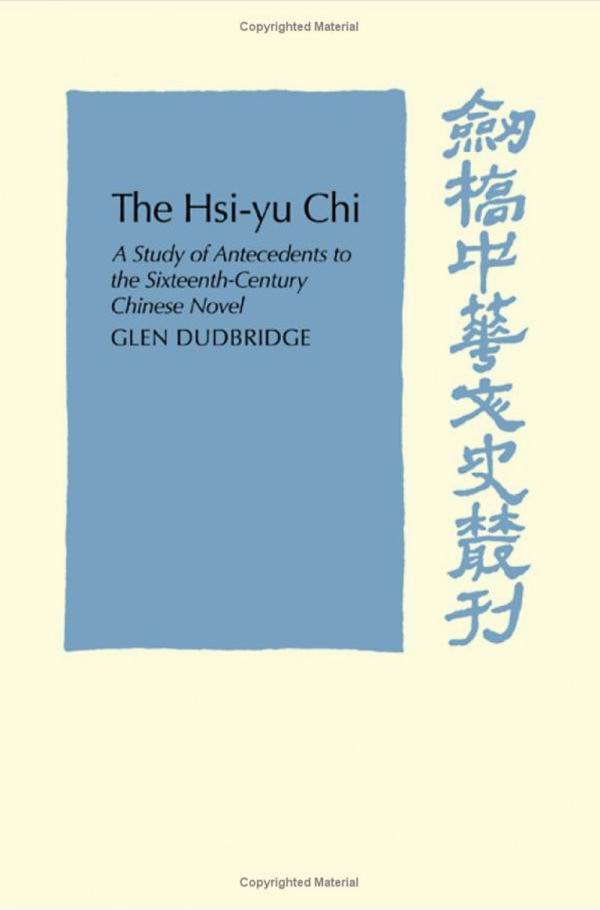
《〈西游记〉:一部十六世纪中国小说的前文本研究》
基本无视海外西游记研究的成果,是《跨文本研究》这部书里较严重的问题。
在前面的诸多讨论里,我们已经看到杜德桥、余国藩、浦安迪、中野美代子等海外研究者关于西游研究的真知灼见。这个名单还可以成倍扩展。然而在《跨文本研究》里,无论是正文还是参考文献部分,均未提及上述学者的贡献。只有第六章“个案考察之二”里,才引用矶部彰关于“刘全进瓜”故事的一篇论文(脚注,未收入参考文献目录)。
“直至20世纪80年代,‘西游学’界并没有明确以‘西游故事’为专门对象的研究成果。”(赵毓龙,第3页)类似这样的论断,可以说非常有失公允。胡胜撰写的序言声称:以百回本为中心的研究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之一,是“最终蜕变为百回本情节的故事是如何演化”。例如鬼子母的传说,就是“以往学界研究的盲点”。赵毓龙先生这部分论证资料详实,确实极具启发。尤其是分析清西游戏《昇平宝筏》对杨本杂剧“鬼母皈依”故事的继承,饶有趣味。但杜德桥1970年的巨著《〈西游记〉:一部十六世纪中国小说的前文本研究》(The Hsi-yu chi: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-Century Chinese Novel),就已经分析过鬼子母在西游故事演化中的作用,并明确提到杨本杂剧里出现过“鬼子母-红孩儿”的母子关系。所谓“盲点”并不存在。杜氏的《前文本研究》,是近几十年来西游研究者无法漠视的一道里程碑。更不用说他的《书籍、故事与俗文化:中国论集》等著作,还将研究范围继续扩大到与西游文化相关的戏剧、民俗和宗教祭祀等领域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,海外学界以杜德桥的西游研究为肇始,陆续形成相关研究。比如说,柳存仁、浦安迪、余国藩、中野美代子、邵平和王岗对百回本宗教寓意的研究;矶部彰的《西游记》成书史和接受史研究;夏志清、陆大伟对中国小说文类的研究;梅维烜对唐代变文和宗教绘画戏曲关系的研究;欧大年的宝卷研究;田仲一成的中国戏曲史研究,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。这些学者不仅彼此参考最新研究成果,对中国国内研究动态也极为关注。
或许正因为缺乏足够的外部参照,《跨文本研究》里的一些论述,才显得有些武断。例如,书中谈到敦煌石室的音写本《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序言(原文误为“菠萝蜜多”),即前面所说S.2464 卷子里的内容时,不仅没有提及梅维烜的最新研究成果,也没有提到陈寅恪更早的研究,或徐文堪的汇总评述文章。作者认为这个序言“叙事性不强,神异性有余,而戏剧性不足”,不如《独异志》里罽宾国老僧口授《多心经》的故事,而后者才是“颇具品位的小说话语”(赵毓龙,50-52页)。这显然没有抓住西游故事虚构化进程的重心。
“不管是西游戏,还是西游说唱,都不是百回本的注脚,也不必承担‘表现、传达出小说所具有的哲理内涵’的义务。”(赵毓龙,第9页)这句话的后半段内容也有待商榷。中国戏曲与宗教祭祀的关联性很强,对小说的形成也至关重要。夏曾佑在1903年即已指出:“其穷乡僻壤之酬神演剧,北方之打鼓书,江南之唱文书,均与小说同科者。”不消说《二郎宝卷》等说唱类型的民间宗教文本,更蕴含着不亚于百回本的“哲理内涵”。梅林宝(Mark R. E. Meulenbeld)在讨论《封神演义》的专著里,曾专门分析过明代小说与“酬神演剧”间的关联。
目前海外西游研究著述的汉译现状,相对还算乐观。前面讨论过的专著,许多已经有中文译本。梅新林、崔小敬主编的《20世纪〈西游记〉研究》,曾收入杜德桥、矶部彰、太田辰夫、尼科里斯卡娅的论文,也时常被人引用。但国内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对理论训练和外语资料的忽视,这种现象确实也存在。
从近年较活跃的学者著述来看,蔡铁鹰在《〈西游记〉成书研究》里,零星提到了太田辰夫、矶部彰和中野美代子。竺洪波在《四百年〈西游记〉学术史》里列举了九十页的研究论著和论文索引,其中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著不足十部,皆为中译本,并且遗漏了杜德桥和余国藩这两位泰斗级学者。至于国外论文的参考数量,则更是寥寥。竺洪波论文《西方文论视阈中的〈西游记〉成书考察》的英文摘要里,“视阈”这个阐释学术语被译成perspective,而不是更常见的horizon。引用的西方文论著作只有萨莫瓦约著、邵炜译的《互文性研究》和詹明信著、陈清侨等人译的 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》。这与海外研究者的资料运用范围和程度相比,显得极不相称。
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来看,中华书局编辑李天飞的《西游记》研究别具一格,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前段时间,林小发(Eva Lüdi Kong)的《西游记》德译本成为热门话题后,李天飞为之撰写评论文章。文章开头提到亚瑟·韦利的《西游记》英文节译,随后又数番引用英译内容并评点,却没有标明译文出处,颇让人误以为这就是韦利的译文。但对照之后才发现是詹纳尔以《西游证道书》为底本的译文。虽然只是报刊和微信公众号文章,但作为专业学者和编辑,这样的做法仍是欠妥。
关注海外研究与译介,当然要保持文化主体性和审慎批评态度。随着专业细分程度的加深,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,反而容易产生新的信息屏蔽与隔阂,以及知识群体的部落化或村寨化。如何突破信息村寨化的局限,如何效法向海外传递微言大义的圣保罗(St. Paul)而不是成为山炮,是当代知识者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。
最后想说的是,《跨文本研究》里还存在一些语言表述上的问题。比较突出的是使用了过多的比喻。这些比喻虽然可以带来直观效果,然而在理论分析过程中,却不仅干扰概念理解和分析进程,而且相互冲抵,造成喻体和本体的严重不匹配。例如,书中仅仅为了比喻不同时期和文类的故事演化,就相继使用“生物群落”“漏斗”“五线谱”“车厢”“绦虫”“化蛹”“细胞”“蚯蚓”等意象,让人眼花缭乱。但这些比喻并非在所有场合都妥帖恰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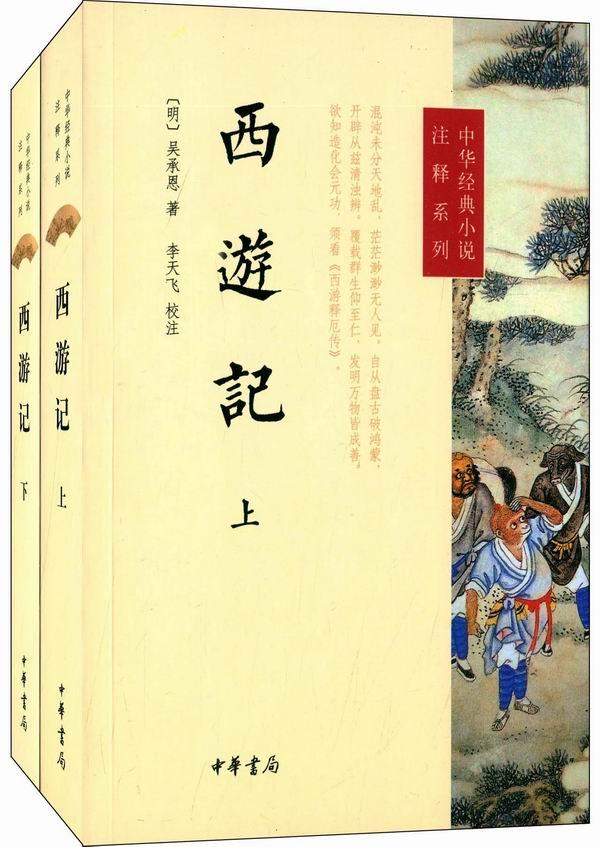
李天飞校注《西游记》
经典题材的研究,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历程。文本内外的复杂关联、批评与理论的经年累积、不同学科的交叉审视、研究方法的改进、材料搜集的困难,种种问题,可谓“山高路远坑深”。
作为西游故事的忠实拥趸,不揣冒昧,提出以上意见,是希望著作者能够认真考虑或许存在的合理意见成份。
至于这部著作的精彩之处,相信各位读者可以在阅读时自行领略。
现当代文学批评经常使用“观众”(audience)这个名称来取代传统的“读者”(reader)概念。百回本,或文本阅读模式,未必就是熟稔西游故事的唯一渠道。“观众”一词,可能更适合描述历史和当前的广大受众。而在“观众”眼里,西游故事的演化面貌,或许始终可以在七十二变的可能性之外,再增添一次想象的机会。






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7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7号